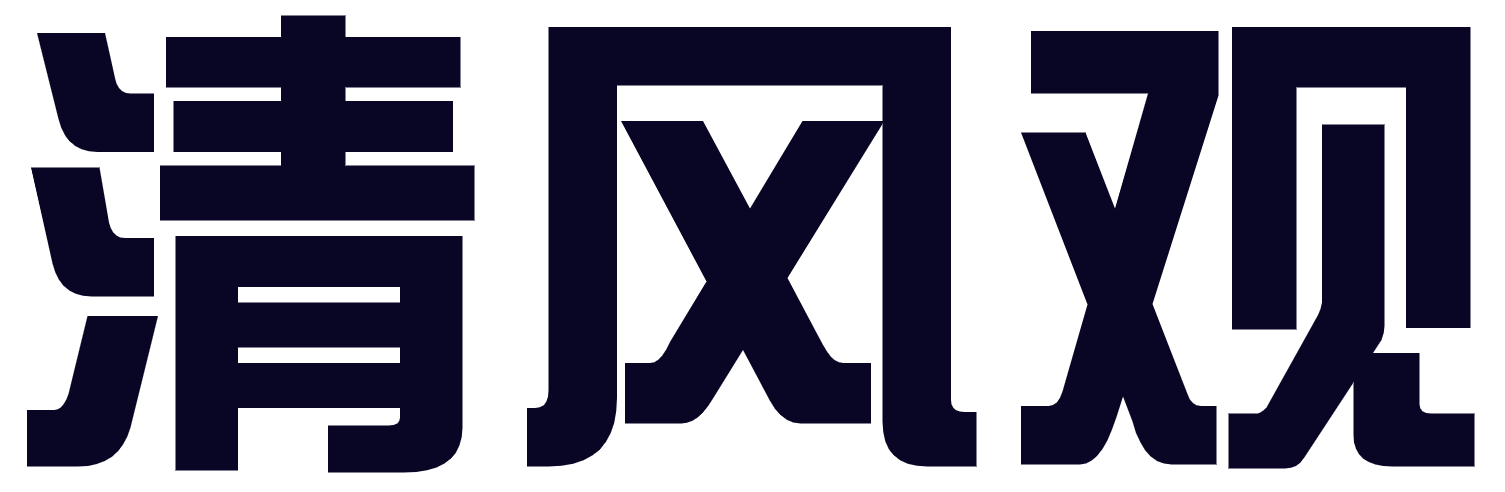Yin-Yang Philosophy Found in the Excavated Silk Version of Inner Canon of Huang Di
作者简介:白奚,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山东 淄博 255000;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48
原发信息:《文史哲》第20212期
内容提要: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将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运用于指导社会活动,提出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四项内容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逐步得到了细化和丰富。从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到《吕氏春秋》,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呈现出一条连续的、清晰的、不断推进的发展线索。研究者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就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因为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吸取了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说,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离不开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黄帝四经》/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阴阳家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16ZDA106)、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19JZD011)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回顾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在六家中对道家最为尊崇,但其所论道家并非老庄道家,而是汉代流行的黄老道家,学术界对此早有共识。太史公从道家同百家之学的关系角度概括其学术要旨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①,其中阴阳家列于首位,可见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此种关系具体如何,由于材料缺乏,人们往往语焉不详。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为厘清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新材料。
帛书《黄帝四经》被认为是战国黄老道家的奠基之作或代表著作②。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出土文献的书名、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上,在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讨论了其与老子思想的关系、道论哲学、法治思想、形名理论,以及道论与法治思想的关系等等,对其中的阴阳思想则基本没有予以特别关注。
随着研究的推进,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政治哲学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的阴阳刑德思想也开始受到重视③,甚至被认为是《黄帝四经》的核心思想④。在中国古代史上,刑与德很早就被确认为治理国家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在《尚书》《周礼》《左传》中,刑与德大体上是并用、并重的,还出现了“三德”“五刑”“明德”“常刑”等较为固定的提法。儒家学派创立之后,于两者中突出了德的重要性,刑被置于不得已而用之的地位,在《论语》中还对两者的得失优劣进行了比较和论述。刑德的话题在战国时期更为流行,这可能与法治的时代潮流有关。从传世战国典籍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商君书》《文子》《荀子》《韩非子》等,承接了《尚书》以来的传统,它们或对刑与德各有偏重,但都与阴阳的思想无涉。另一种是《管子》和《吕氏春秋》的以阴阳论刑德,引进了阴阳的消长作为刑德施行的天道根据,其理论的重点已转移到“人与天调”⑤理念下的刑与德如何施行与交替为用。
起始于《尚书》时期的刑德理论,是从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为政经验,大体上是一种认定,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论证。《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运用天道阴阳的理论为刑德的施行进行了哲学论证,使之获得了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支撑。《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同其他战国诸子的刑德论显然不在同一个理论脉络上,以往的研究通常都视之为阴阳家的理论而未予深究。直至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对照起来可以看出,其中的阴阳思想同《管子》和《吕氏春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理论联系和递进的发展脉络,而《黄帝四经》中所见是以阴阳论刑德的最早材料⑥。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应对这三部著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帛书《黄帝四经》将阴阳观念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阴阳理论做出了重要的推进。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是其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对后来兴起的阴阳家学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这四项内容分别进行系统的梳理,并结合传世文献,理清战国中晚期阴阳思想发展的这条重要线索,以补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足。对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所开发的阴阳思想同阴阳家学派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目标。
二、四时教令
“四时教令”语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⑦,太史公认为此说虽“未必然也”,但因其“序四时之大顺”,故而“不可失也”。而其所以“不可失也”,是因为“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⑧。可见,四时教令的核心思想是顺应“天道之大经”,为人类社会确立“天下纲纪”。
《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思想,是所有传世典籍和出土简帛佚籍中最早的也是最为全面的表述。
四时教令思想溯源于春秋以来盛行的阴阳观念。阴阳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特色观念,《黄帝四经》对这种传承已久的观念作出了关键性的推进。从《左传》《国语》等传世典籍中的记载来看,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只是被用来解释星陨、地震等异常和灾害性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通常都被解释为自然界中的阴阳失衡所导致的,而与人的行为无关,人只是自然灾害的承受者。《黄帝四经》将阴阳观念引入社会领域,主要用于解释和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提出了系统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步十分关键,是对阴阳观念的重大推进。《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思想以阴阳观念为理论基础,强调人的社会行为必须依循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消长之序。这种强调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同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的阴阳观念所没有认识到的,这表明阴阳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是《黄帝四经》对阴阳思想的重要推进。
在《黄帝四经》中,四时教令的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此即所谓“敬授民时”;一是被用来指导政治活动,此即所谓“因天时”。
“敬授民时”,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⑨又见《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家的论断,其言曰:“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⑩其具体内容即上引《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就是自觉利用阴阳四时的理论,顺应一年四季的自然节律以安排农业生产。《黄帝四经》用阴阳观念解释季节的变化,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消长的结果,把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关于季节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经验性认识上升到天人关系的高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为顺天授时或敬授民时的思想。如《经法·道法》曰:“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11)以男农和女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被提到了“万民之恒事”的高度而与“天地之恒常”并列,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农业生产堪称人类社会生活之永恒的主题。“生杀”指草木的生长与凋零,是阴阳二气的作用,柔刚是阴阳表现出来的两种相反的气质或特性,而四时和晦明都是阴阳二气消息盈缩运动变化的表现。作者将这些同男农女工等农业生产活动对应起来,表明他们认识到二者之间遵循着共同的规律。此类认识,《黄帝四经》中还有很多,不烦多举。这些看似经验之谈的话语,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是迄今所见关于“敬授民时”理论的最早表述。
四时教令的理论在《黄帝四经》中更多的是被运用于政治领域,“因天时”的命题可以视为其集中概括。“因天时”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用来作为君主施政的依据和准则。后来的很多战国诸子著作都接受了“因天时”的理论,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提出“因人情”的理论,在百家争鸣高潮时期影响很大。同敬授民时的农业生产理论相比,从天道观的高度提出和论证政治理论的内容,在《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理论中占有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地位。
《黄帝四经》中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是从谈论抽象的天道阴阳问题开始并引出的,有关政治活动的一切内容,无不被认为同阴阳四时之序密切相关,于是,“因天时”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就被提了出来并反复强调。“因天时”是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黄老道家的很多政治主张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这一命题就是《黄帝四经》首先明确提出的,《经法·四度》曰:“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12)《十大经·兵容》亦曰:“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13)《帝四经》认为,不但农业生产要“因天时”,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必须“因天时”,《经法·君正》曰:“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14)在这里,国家的政治活动被概括为“文”和“武”两类,“文”的内容是“养生”,“武”的内容是“伐死”,而“天有死生之时”则是文武之政实施的天道观依据,这其中显然贯穿着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道家式的思维方式。这种在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在《黄帝四经》中表述得十分丰富和集中。
“因天时”是一个基本的大的原则,但毕竟比较笼统,为了使这一基本原则更有可操作性,《黄帝四经》的作者又提出了一系列配套的细化的原则,来保障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天时具有循环的性质,每一个循环的周期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称为“天极”“天当”,圣人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和利用好这个关节点,正如《经法·国次》所言:“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15)“天极”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点,把握这个点是极难的事情,只有圣人才能够很好地做到。把握“天极”必须注意两点。其一是“尽天极”,《经法·国次》曰“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16),天极未尽便采取行动就是“擅天功”,必然招致失败。其二是勿失“天极”,“毋失天极,究数而止”(《称》)(17),错失“天极”,不但时不再来,而且还会招致祸殃,如《经法·国次》所言:“过极失当,天将降殃。”(18)而无论是未尽天极还是错失天极,在《黄帝四经》中都被认为是“逆天时”,都会招致“天刑”“天殃”“天诛”等惩罚。《黄帝四经》中对此类违反天时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兹不赘述。
四时教令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具有理论基础的地位,《黄帝四经》阴阳思想的其他内容都是由此推展出来的。“因天时”是四时教令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全部《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是《黄帝四经》对古代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慎子》《管子》《文子》《吕氏春秋》等战国时期的重要典籍中都有对“因天时”的阐述发挥。
四时教令的思想在《管子》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管子》用阴阳的推移解释四季的变化,其言曰:“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19)因而君主在不同季节的施政措施必须与阴阳消长的节律相协调。具体措施如《七臣七主》篇所言,明主有“四禁”即四时之禁令:“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20)《管子》将诸如此类的四时禁令概括为“务时而寄政”(21),以求“人与天调”(22)。同《黄帝四经》相比,“因天时”的思想在《管子》中得到了提升和细化,也具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
在《吕氏春秋》中,四时之禁令又被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管子》中的“明主”也换成了“天子”,“天子”从穿衣吃饭到发布政令,在每个月中均各有宜忌和具体规定,这在该书的“十二纪”中有详尽的记述,兹不赘举。作为该书总序的《序意》有言:“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23)“十二纪”是《吕氏春秋》全书的写作纲领,四时教令作为“十二纪”写作的理论框架,其对《吕氏春秋》全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从《黄帝四经》的“因天时”,到《管子》的四时禁令,再到《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时教令思想深化发展的轨迹。
三、阴阳刑德
阴阳刑德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四时教令理论在治国这一关键领域的应用,也是对四时教令的理论提升。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提出了以“因天时”为核心的原则,为人的社会活动确立了天道观方面的指导;而阴阳刑德理论关注的重心则集中在了四时教令理论在政治生活这一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因天时”的原则在政治活动中的具体实施。
“刑”即刑政,指的是刑罚、法令等严厉的、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德”即德政,指的是仁德、劝赏、教化等温和的政治手段。刑与德作为施政的两种基本手段,是既相反又相辅相成的,在具体的运用中往往需要交相为用,这一点很早就被上古时代的统治者认识到,并成为西周以来重要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验,《尚书》《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都有很多刑与德并举、并用的记载。不过在这些早期的政治经验中,刑与德还只是作为纯粹的治国方略出现,尚未与天道阴阳联系在一起来思考。《黄帝四经》首创阴阳刑德的理论,把天道之阴阳与政治之刑德联系并对应起来,从而使刑德具有了形而上的理论支撑。
《黄帝四经》的阴阳刑德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十大经·姓争》提出的“刑阴而德阳”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盈缩消长的规律以及“天地之道”和“人事之理”之关系的认识。作者认为,为政之所以要刑德相辅并用,是因为人事必须符合天道,天道有阴有阳,为政就要有刑有德。作者还提出“天德”和“天刑”的概念,把德与刑解释为“天”的特质的一体两面,从天道观的高度来论证德与刑相辅并用的必然性,其言曰:“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24),从而根据宇宙间最基本的自然现象阴阳四时的流布运行规律,为刑与德的施行确立了根据和法式,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了刑德与四时相配的理论模式。这种刑德与四时相配的理论在《十大经·观》中表述得最为集中和经典,比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25)又曰:“夫并(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26)作者把一年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段,春、夏两季是阳气上升的时节,故称之为“阳节”,秋、冬两季是阴气渐盛的时节,故称之为“阴节”。在作者看来,春夏两季阳气充盈,万物萌发生长,宜施行温和的政治——“德政”,以符合“阳节”;秋冬两季阴气渐盛,万物肃杀凋零,宜正名修刑,施行严急的政治——“刑政”,以符合“阴节”。作者又把这一思想明确地概括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如此一来,君主施政就有了天道观方面的指导和依据,一年中何时实行德政何时实行刑政就不再是无章可循的了。不难看出,这一主张所体现的深层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十大经·观》还提出“先德后刑”的主张,天地间阴阳二气的赢缩消长表现为四时的更替,由于四时中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就决定了德政与刑政的先后次序:“先德后刑”,并称此为“顺于天”。“先德后刑”,是说一年之中要先实行德政后实行刑政,先后次序不能错乱,目的是“养生”,让万物和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到了秋冬两季再实行严厉的刑政。这种“先德后刑”政治主张的天道观根据就是阴阳二气的盈缩消长规律。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四经》这里讲的是德与刑两种治国手段的使用在一年中有先后之序,德之于刑只具有时序上的优先性,且德与刑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又是交替为用的,二者之间其实并无轻重主次的关系。这同汉代董仲舒那种强调德政之于刑政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董仲舒显然是以儒家的立场来吸取和改造了《黄帝四经》的阴阳刑德思想。
“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和“先德后刑”为一年中德政和刑政的施行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尚需要进一步细化,《十大经·观》提出了“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27),使这些原则性的指导思想落实到可具体操作的层面。“赢”的初始义是“有余”,亦释为“溢”“过”,《史记·天官书》曰“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28),《汉书·天文志》亦曰“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29),指的是星宿的运行超出了其应居的正常位置(“舍”)。考虑到《十大经·观》中“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两句出现的段落讲的是“地气”“夜气”等阴阳之气在不同时节的“萌”“滋”“长”“闭”等变化规律,此处的“赢”从阴阳之气的赢缩消长的方面来理解更为妥当。“赢阴”指的是阴气在冬季(具体来说就是冬至日)的发展达到并超出了极致的状态,此时阴气开始衰退而阳气开始萌生,统治者应该不失时机地“布德”,开始实行温和的德政。“宿”在此处当通假为“缩”,以与“赢”相对,“赢”与“缩”对文,为古籍中所常见。“宿阳”指的是阳气在夏季(实际上是具体到夏至日)的发展达到并超出了极致的状态,此时阳气开始收缩而阴气开始萌生,统治者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在此关节点上开始实行严急的刑政。时下研究《黄帝四经》的学者们大都将“赢”解释为“盈”,谓阴气盈满之时便开始衰退而阳气开始萌生,此时施政就应该“布德”,这样的解释当然也很圆满通顺,毕竟“盈则溢”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困难的问题出现在与此相对的“宿阳”上,学者们大都把“宿”字依其本义解释为“止”,也有人释为其引申义“久”,这些解释虽然也大体可通,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人看来,无论是星宿的运行还是阴阳之气的变化,从来都不存在“止”的情况,《庄子·天下》所谓“日方中方睨”(30)人们理解和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宿”的引申义“久”用于此处也不稳妥,“久”具体指多长时间?如何把握?若谓“久阳修刑”显然不大具有可操作性。再者,“宿”与“缩”通假亦不乏其例,《庄子·徐无鬼》“枯槁之士宿名”(31),俞樾《诸子平议》按“宿,读为缩”(3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宿,字或作蹜”(33)。“蹜”即“缩”的另字,《集韵·屋韵》曰:“蹜,通作缩。”(34)所以,“宿阳修刑”乃是阳气收缩之时即开始修刑政之义。
“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的提出,表明《黄帝四经》的作者对物极必反的法则和对立转化的规律有深刻的认识。《经法·四度》曰“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35),认为物极必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律。《经法·四度》还提出“极阳杀于外,极阴生于内”(36)的说法,这是对物极必反法则的更深入具体的阐释。“杀”指草木的凋败枯萎,“极阳杀于外”是说,当阳气发展到极盛时便开始转衰,阴气转盛,这种变化是通过事物的外表呈现出来的,那就是草木始“杀”;而当阴气发展到极致时,阳气就开始转盛,这种变化发生于事物的内部,那就是万物内部萌发的生机,而从事物的外在往往不易看出。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必须依此而行,那就是“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前者是说,当冬日已尽,阴气发展到极致时,阳气即开始萌发,此时正是万物孕育生机的时候,应开始布施仁德;后者是说,当夏日已尽,阳气停止发展时,阴气便开始转盛,此时正是万物由盛转衰的契机,应开始修饬刑罚。这就是刑德转换为用的天道观根据(37)。
在《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阴阳刑德的理论最具可操作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对其后战国诸子的治国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管子》对阴阳刑德的理论有更深入的论证。其《四时》篇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38)并将《黄帝四经》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进一步细化为“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39)。《形势解》所言更加具体:“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40)《四时》甚至还提出,施行符合该季节阴阳节律的政令,对阴阳二气的运行有辅助作用,如夏季“其事: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助阳气”(41)。这些材料表明人们对一年中阴阳二气赢缩消长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人的行为同自然节律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显然,在阴阳刑德理论的背后并起决定作用的,是更为深刻的天人合一观念。
《吕氏春秋》将德与刑更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此即所谓“月令”。我们仅以仲春和孟秋两月为例来比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阴阳刑德是如何落实在每个月中的:“仲春之月……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42)“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43)
从《黄帝四经》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经《管子》的“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到《吕氏春秋》的十二月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阴阳刑德思想发展的轨迹。《礼记·月令》照搬了《吕氏春秋》的十二纪,足见汉代儒家对黄老之学的阴阳刑德理论接受程度之高。
四、阴阳灾异
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阴阳灾异可以说是一个特色理论,其主旨是用阴阳理论解释自然灾异的发生,强调人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的失当可以导致阴阳失序而引发灾异,主张用人事服从天道以实现阴阳协调有序的方式来避免灾异。这个理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视自然灾异并试图对自然灾异作出解释,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中,对自然灾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另一种则是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解释。《黄帝四经》延续的是用自然界自身的原因解释灾异的古老传统,并运用业已获得长足发展的阴阳理论解释灾异,这种对灾异的解释方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阴阳理论。学者共知,自西周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用阴阳失序解释灾异的理论,《黄帝四经》传承的正是这一理论路向,并做了关键性的推进,那就是把自然界的天地阴阳同人类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联系了起来,强调和关注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灾异的出现是阴阳失序,而阴阳失序的原因则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误。这一推进的理论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为阴阳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使其得以在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问题上大显身手,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最终极大地促进了阴阳理论的发展。显然,阴阳理论如果始终局限在解释自然现象的领域,就只能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中国古人最为重视的政治哲学理论,其在后世的延续、发展和历史地位就不容乐观。其次,阴阳理论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也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一条十分便捷有效的渠道,可以直接为政治主张提供天道观方面的形上根据和理论支持,使得政治主张得以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极大地提高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在先秦那个列国激烈竞争并渴求治国良方的时代,某种政治理论是否披上天道阴阳的神圣外衣,其对列国君主的影响力是大不一样的。再次,从哲学思维层面来看,这一推进丰富和深化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思维一以贯之的深层观念,无论是在原始宗教和天命观占主导地位的三代时期,还是在天命观渐趋衰落而人文精神崛起的春秋时期,天人合一都是古人思想中最为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最为稳固的深层内容,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黄帝四经》以天地阴阳言说社会政治,赋予了天人合一这一古老传统以新的内容,是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延续、开拓和深化。最后,它在规范、制约统治者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中国古代从来都是一个君权至上的社会,对君主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手段,对于君主行为的影响,无非是正面的引导和反面的规劝两种基本方式。反面的规劝通常可分为提醒和警告两种,无论是提醒还是警告,都围绕着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是“民心”,一个是“天意”,告诫统治者要顺应民心和天意而不能违背。所谓天意实际上是虚设的,相信与否和重视与否全在于统治者如何看待,缺乏可以看得见的证据。于是,利用自然灾异,把自然灾异说成是天意的警告,便为古人所常用。《黄帝四经》把自然灾异的原因解释为政治失误导致的阴阳失序,这种解释比起此前的解释来更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对君主施政行为的规范和纠正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而从规范和警告统治者行为的方面来看,可谓增添了新的制约内容和手段。
《黄帝四经》的阴阳灾异思想非常丰富。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天地间的阴阳失调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也是社会政治的刑德失序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天地间阴阳四时的运行和人类的社会活动遵循着共同的节律(“赢”“绌”),人事(“事”)必须顺应天时(“时”),以符合天时之“阴阳节”,并对违反阴阳法则的行为提出了警告。《十大经·观》曰:“其时赢而事绌,阴节复次,地尤复收,正名修刑,执(蛰)虫不出,雪霜复清,孟谷乃萧(肃),此灾□生。如此者举事将不成。”(44)“赢”为生长,“绌”为收缩,“阴节”即秋冬季节。此句是说,春夏两季是阳气上升、万物生长的季节,应实行宽厚温和的政治,如果此时实行“正名修刑”之类本应在秋冬时节实行的严厉的政治,就违背了阴阳消长的节律,就会促使阴气不正常地发展,致使地气收缩,表现为昆虫蛰伏不出,霜雪再现,谷物凋敝等本应秋冬才有的现象,造成灾害。同样的道理,“其时绌而事赢,阳节复次,地尤不收,正名施(弛)刑,执(蛰)虫发声,草苴复荣。已阳而有(又)阳,重时而无光,如此者举事将不行”(45)。秋冬两季阴气占主导地位,本应实行严急的政治,若此时刑罚弛懈,实行宽仁的政治,就会使得本已停止发展的阳气不正常地发展,使地气不能收缩,将会出现天气炎热,蛰虫不伏,草木复荣等反常现象,造成灾害。这种用阴阳四时解释灾异的理论,其关键在于“时”和“事”是否协调一致,强调的是人事必须顺应天时。可见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灾异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社会政治的刑德失序是天地间阴阳失调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理论路向被《管子》所承袭,并加以发挥和细化。《四时》篇对此所论最详,作者认为,四时各有其政,不可错乱,否则就会气候反常,导致灾害,如“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46),“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47)。作者总结说,“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48),这些“大殃”,包括日食、月食、彗星见、风与日争明等灾异现象,甚至还会导致军事行动等国家大事的失败,这同《黄帝四经》的看法是一致的(49)。
《吕氏春秋》所论比《管子》更进一步,对刑德失次导致灾异的认识更加细密,具体到了每一个月。例如同是春季,三个月中各有不同表现:“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50)“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煗气早来,虫螟为害。”(51)“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52)值得注意的是,刑德失次不仅可以导致天灾还可以导致人祸,这是《黄帝四经》《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共识,但在前二者那里还只是“举事不成”“作事不成”,即征伐他国等主动行为的失败,而在《吕氏春秋》中,还包括了“寇戎来征”“兵革并起”等被动性的灾祸,在《吕氏春秋》作者眼里,这类灾祸归根到底还是刑德失当引发的。
五、阳尊阴卑
阳尊阴卑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的另一个特色理论,集中的表述见于《黄帝四经·称》,其言曰:“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53)作者根据“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和“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的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和关系概括为阴和阳两类,属于阳的一类被认为是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属于阴的一类则居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决定这一切的是“阴阳大义”,即人道取法于天道,天道之阴阳决定了人道之尊卑贵贱。在作者列举的这些对应的现象和关系中,除天地、春秋、夏冬和昼夜之外,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和伦理关系,这表明作者此处论述阴阳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给人间的政治生活特别是人伦秩序这一作者真正最为关切的问题寻找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根据。
阳尊阴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中国古人的基本观念之一,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帝四经·称》中这段话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而且相当的系统、全面,是研究阳尊阴卑思想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黄帝四经·称》以阴阳明尊卑之大义,是对尊卑上下这一远古就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深层观念的第一次理论化的表述,第一次从天道阴阳的高度,对尊卑有序、贵贱有等这一中国古人心目中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论证。《称》的阴阳尊卑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古人看来,尊卑有序、贵贱有等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的基本秩序,只要这个秩序不乱,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行。反之,这个基本秩序被打乱,社会必然出现危机,正是由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孔子才发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慨叹。在这个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等级序列里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承担着与此相应的社会义务。这个位置或角色是根据血缘、出身、受教育程度、贤能程度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而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定位,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认可和接受这个角色和定位,并根据这个角色和定位来承担与此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这种差异鲜明、等级确定的社会是公平合理的,尊卑上下、长幼亲疏各有分寸而不淆乱,就是理想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构想在战国晚期的荀子特别是两汉的儒家著作中有充分的论证,不过荀子等人都是根据“礼”“名分”等儒家的理念来阐发和论证等级秩序的,《黄帝四经·称》早在荀子之前就系统地提出了尊卑等级的思想并从天道阴阳的高度进行了形上化的哲学论证,可见其理论价值之高。尊卑等级的思想同天道阴阳思想的结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说这两种思想本身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双方的理论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具体来说,社会上的尊卑等级观念首次获得了形而上的哲学根据,找到了最佳的论证方式;天道阴阳的思想也找到了论证人道秩序的最佳结合点,发挥了最大的理论效用。
阳尊阴卑的思想可以说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最独特的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独见于《黄帝四经》,《管子》和《吕氏春秋》中也未见阳尊阴卑的思想。阳尊阴卑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大量出现,比较《黄帝四经》和《春秋繁露》的阳尊阴卑思想,无论是基本理念、思维方式、思想内容乃至语言表述,都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乃至雷同之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思想上的源流关系,后者当是直接承自《黄帝四经》。以往我们在提到阴阳尊卑思想的时候,都是把目光集中在董仲舒的相关思想上,若不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我们就无从知晓这种理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
六、黄老道家与阴阳家的关系(54)
笔者认为,以上讨论的帛书《黄帝四经》中所见四时教令等阴阳思想,是先秦黄老道家将阴阳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与伦理领域而做出的思想创造,是黄老道家对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做出的重要推进。笔者的这一观点必然会联系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黄老道家和阴阳家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通常都把《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归之为阴阳家或受阴阳家的影响(55),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不够严谨的,等于是认定在《黄帝四经》之前就存在着一个独立完整的阴阳家学派。笔者的观点是:四时教令等阴阳理论是战国中期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创造,为战国晚期的阴阳家所吸取,成为阴阳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由如下:
第一,阴阳家是先秦重要学术流派中最晚出现的一家。一般来说,某家之学之所以能够称为“家”,须具备代表人物或创始人、代表著作、独具的思想体系、传承系统等条件、要素,用这些条件、要素来衡量,阴阳观念虽产生甚早,但一直比较零散,还不能称为阴阳家,直到战国晚期的邹衍才开创了学派并有人传承,此乃学界定论。而此时,道家黄老之学,至少已活跃了半个多世纪。
第二,现存典籍中所见到的邹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并没有四时教令等思想内容。邹衍的著作早已亡佚,我们虽然缺乏确凿的、直接的材料来证实其中包含了四时教令等思想,但仍然有迹可循,可以间接得到证实(56)。据前引《论六家要指》和《汉书·艺文志》论阴阳家思想的要旨是“序四时之大顺”“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即所谓四时教令。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既然四时教令等思想是阴阳理论的主要内容,邹衍作为阴阳理论的集大成者,那他的思想中就理应包含有这部分内容。但退一步说,即使邹衍的著作中确有四时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他的首创或独创,因为在他之前的道家黄老之学中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四时教令等思想,《黄帝四经》《管子》早于邹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
第三,《黄帝四经》是道家黄老派的奠基之作,其内容反映了战国中期黄老道家的思想成果,其中的四时教令等思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以阴阳推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史料,明显早于邹衍。《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早期的阴阳观念提升为一种哲学理论,这对于阴阳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显然,阴阳观念如果一直停留在用来解释异常的自然现象的阶段,就不会大行于世并发展为一家之言。可见,阴阳家终能成为“六家”之一,离不开《黄帝四经》的理论贡献,也离不开《管子》《庄子》外杂篇等黄老道家著作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57),“明于五德之传”(58),他的学说就是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而《黄帝四经》中却只见阴阳不见五行,这说明《黄帝四经》成书的时候,阴阳说与五行说尚停留在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的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尚未合流为阴阳五行说(59),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已在《黄帝四经》中出现并已经比较成熟了。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于《管子》,学界对此大体无异议(60),没有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合流,就不会有阴阳五行家的出现。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派,离不开《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贡献。
第五,《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体都有传承和丰富发展,《管子》是战国中期成书的,早于邹衍,可以看作是《黄帝四经》与邹衍之间的中间环节。如果齐人邹衍的已佚学说中包含有四时教令等内容,也应该是通过齐文化的代表著作《管子》传承而来。
第六,《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文献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四时教令、阴阳灾异等思想,但这些都是阴阳家出现之后的作品,这些思想有可能是传承自阴阳家,但也很可能是直接传承自黄老道家,这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我们不应见到关于阴阳的思想就简单地认定为是传承的阴阳家。以《吕氏春秋》为例,虽然其成书时阴阳家已经自成一家且十分流行,但其“十二纪”同《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联系和发展轨迹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其十二月令是从《黄帝四经》和《管子》的相关理论发展细化而来,这是难以否认的。
第七,黄老道家的某些同阴阳观念有关的思想乃是自家所独有的特色理论,如阳尊阴卑的理论就仅出现在《黄帝四经》中,邹衍的遗说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没有出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阳尊阴卑的思想大加发挥,这部分内容只能是直接承自黄老道家,同阴阳家并不相关。
第八,古代的重要学派创立之前,其思想理论通常都经历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阴阳家也是这样,由早期的“阴阳观念”发展到帛书《黄帝四经》时期的“阴阳思想”,最后由邹衍创立了“阴阳家”学派,这一发展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我们应该明确地区分“阴阳观念”“阴阳思想”和“阴阳家”这几个概念,而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以免淹没了《黄帝四经》《管子》等黄老道家的理论贡献。
总之,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的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思想创造,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观念就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接受了这些思想,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使之成为阴阳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家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例如董仲舒)的相关思想时,都把它们看作是受阴阳家理论的影响,从阴阳家的成熟形态及其历史影响来看,这样的看法固然是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理论在成为阴阳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曾经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而长期存在。
注释:
①《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9页。
②此一观点是较早研究帛书《黄帝四经》和黄老道家的学者们提出来的,可参考诸如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余明光:《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王博:《〈黄帝四经〉与〈管子〉四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213页。
③这一情况可以从逐渐增多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上看得出来,如荆雨:《帛书〈黄帝四经〉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赖世力:《〈黄帝四经〉阴阳刑德思想述论》,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王佩:《〈黄帝四经〉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李夏:《帛书〈黄帝四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④金春峰提出,“帛书思想的核心是阴阳刑德思想”(金春峰:《论〈黄老帛书〉的主要思想》,《求索》1986年第2期)。崔永东认为,“帛书《黄帝四经》确实是以刑德问题为其理论核心的,并且把刑德与阴阳结合起来,以阴阳作为刑德的自然根据。这便是所谓的阴阳刑德论”(崔永东:《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⑤《管子·五行》,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
⑥正如崔永东指出的,“真正首先合论阴阳与刑德的,当推《黄帝四经》,正是它为刑德提供了自然根据并进行了详密的阐述”(崔永东:《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⑦《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⑧《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6页。
⑩《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4页。
(11)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3页。
(12)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51-52页。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1页。《十大经·观》中也有这句话,“因天时”作“当天时”,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3页。
(1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7页。
(1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5页。
(1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5页。
(17)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82页。
(18)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5页。
(19)《管子·乘马》,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5页。
(20)《管子·七臣七主》,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995页。
(21)《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55页。
(22)《管子·五行》,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65页。
(2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4页。
(2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9页。
(2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2页。
(2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2页。
(27)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2页。
(28)《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12页。
(29)《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第1280页。
(30)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02页。
(31)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834页。
(32)转引自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835页,注6。
(33)转引自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83页。
(34)转引自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第2231页。
(3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51页。
(3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51页。
(37)《淮南子·天文训》曰:“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此语与“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思想意义一脉相承,正可作为注脚。
(38)《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36页。
(39)《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57页。
(40)《管子·形势解》,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168页。
(41)《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46-847页。
(42)《吕氏春秋·仲春纪》,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33-34页。
(43)《吕氏春秋·孟秋纪》,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154-156页。
(4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2页。
(4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2页。
(46)《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42-843页。
(47)《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51页。
(48)《管子·四时》,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57页。
(49)胡家聪先生认为,《管子·四时》中这些阴阳灾异的内容在《黄帝四经》中是“找不见”的,“为《四经》所不取”,这显然是没有细读《黄帝四经》所导致的错误判断。参见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50)《吕氏春秋·孟春纪》,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12页。
(51)《吕氏春秋·仲春纪》,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37页。
(52)《吕氏春秋·季春纪》,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65页。
(5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83页。
(54)本文第六部分的主体内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3日第6版上刊载,本文又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修改。
(55)例如,“帛书论及刑德与节令的联系,显然是受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刘蔚华、苗润田:《稷下学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86页),又如“《黄老帛书》中的阴阳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秦阴阳家思想”(鞠秋洋:《〈黄老帛书〉中的阴阳家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17年硕士论文)。
(56)参看白奚:《邹衍四时教令思想考索》,《文史哲》2001年第6期。
(57)《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58)《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259页。
(59)关于《黄帝四经》早出之论证,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6-108页。
(60)关于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于《管子》的论证,参见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